第七講:竹內好與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會”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七講:竹內好與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會”
–近代日本研究中國新文學力量的興起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徐靜波
主講人介紹:徐靜波: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領域為中日文化關系,中日文化比較。專著有《梁實秋:傳統的復歸》,《東風從西邊吹來-中華文化在日本》,《近代日本文化人與上海(1923-1946)》,《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種形態》,《解讀日本:古往今來的文明流脈》,《困惑與感應: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國圖像1918-1945》等11種,譯著有《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密錄》,《魔都》等16種,編著有《日本歷史與文化研究》等12種。曾在日本神戶大學,東洋大學,京都大學等多所大學擔任教授。現為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的首席專家。
第七講:竹內好與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會”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1934年4月,以東京帝國大學為溫床,日本誕生了第一個以現代中國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團體——“中國文學研究會”,它的核心人物便是竹內好(1910-1977),那一年他才24歲,剛剛從東京帝大畢業,與他共同創建這一研究會的武田泰淳和岡崎俊夫,也是曾經的帝大學生。
何以會在中日關系日益緊張的1934年,在日本會誕生了中國文學研究會這一組織並艱難維系了長達9年的歲月?它在當時和日後的中日文學交流史上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呢?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下這一話題。
大家知道,日本與中國有著十分悠久的文化交往歷史,早期日本列島上的居民是有語言而沒有文字,早期的日本文獻都是用漢字漢文記錄的,10世紀前後,日本語文誕生,但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依然會閱讀漢文漢詩,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了明治中後期(19世紀末)。所以那個時代,稍有教養的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文學都很熟悉。19世紀後半期,西洋文明傳入日本,歐洲人研究學問的方法也漸漸為日本人所掌握,於是日本人就開始運用相對比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早在1892-95年期間,就出現了兒島獻吉郎等撰寫的《支那文學史》,那時中國人自己寫的通史性質的中國文學史還沒有,由此可知日本人很早就開始了對中國文學的系統研究,後來在東京帝國大學等相繼開設了支那文學研究科。不過,那一時期,日本人研究的,主要是古代的、至少是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學,對近代以後的中國,幾乎很少註目。
到了1930年代初,那時的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科的一批青年學生,就對這一現狀很不滿,他們憑著一股年輕人的激情和朝氣,就打算打破這種陳舊的氣氛,在中國文學研究上,開辟出一個新的局面來。那麽,這是些什麽樣的青年人呢?他們的目的只是為了破舊麽?
岡田1933年從東大畢業,武田1931年進入東大後,因參加左翼活動而被警署三次逮捕,此後也就不去上課且未交納學費,事實上也就終止了學業。他們兩人都出生於僧侶家庭(日本的僧人在明治5年也就是1872年獲準可以娶妻食肉),自幼習讀佛經(佛教在6世紀中葉自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傳入日本後,基本上采用漢譯佛經),他從小就對中國古典文學有所觸及,養成了較高的古漢語閱讀能力,較早就表現出了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在高中期間閱讀了《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並去了一家私立學校學習現代漢語,嘗試閱讀胡適、魯迅等新文學家的作品。而岡崎在高中期間,似乎對俄國更感興趣。而竹內則出生於醫師和官吏的家庭,自幼與中國並無家學淵源,他自己曾坦言,進大學後仍無法順利地閱讀古漢語(日語稱之為“漢文”,包括中國的古籍和日本人用古漢語撰寫的文獻),甚至對中國也沒有太多的關切,他之所以選擇這一專業,主要是因為不必考試,進了學校,即使不怎麽去上課,屆時也可順利畢業。事實上,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科,並不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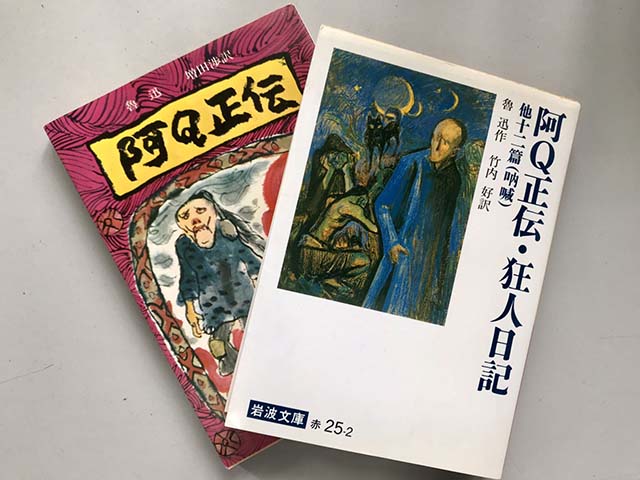
《阿Q正傳》,《狂人日記》日文版
如果這樣的狀態持續下去,大概也就沒有日後中國文學研究會的誕生。這裏,作為該組織領袖人物的竹內好1932年的中國之行,可謂徹底改變了他本人的命運,也是中國文學研究會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機緣之一。這一年的8月,他獲得了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的一半資助,隨一個學生團體經朝鮮半島到中國來旅行,他到中國來的動機,一開始並非出於對中國的興趣和關切,他後來自己曾說: “我那時學籍雖然放在中國文學科,但並沒有真心想要搞中國文學,對中國也沒有什麽興趣。只是因為這次旅行有旅費的補助,便想利用這一制度來滿足一下青年時期特有的放浪癖好。但是到了北京以後,我被那裏的風情和人物所醉倒了。即使到了期限,我也不想回日本,請家人再寄了旅費過來,一個人待到寒風將要襲來的季節,每天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行走。我與中國的結緣,就始於這次北京之行。”① “於是我的想法完全改變了。從此就想真心研究中國,買了若干的書刊帶回來,開始了我的第一步。因為我還無法閱讀漢文,於是就從現代漢語開始。”②
當竹內好決心想要研究中國、尤其是中國文學的時候,他們這些年輕人就立即意識到了日本學界的老舊氣氛,大學的教授,對於正在發生劇烈變革的中國現狀、尤其是五四以後中國文學出現的新氣象,幾乎視若無睹,這使他們感到很不滿。研究會核心人物之一的武田泰淳在1943年回憶說:
“我們從學生時代開始,對漢學這樣的東西抱有反感。與其說是抱有反感,不如說是完全沒有興趣。通過漢學來接觸支那的文化,總不能獲得滿足,在感覺上也很不喜歡。倒也不是說對漢學的本質已經看得很明白,而是對由漢文所籠罩的這種氣氛,由漢學所散發出來的儒教的冬烘氣,怎麽也無法適應。作為日本人來說,應該還有其他研究支那的途徑。…於是我們在昭和九年(1934年)開始了中國文學研究會,對支那的現代文學、支那的支那學者的業績,展開了調查。”③
當然,1930年代初期,日本的文壇或研究界並非對中國的新文學完全視若無睹。事實上,在1920年創刊不久的《支那學》雜誌11月號上就連續刊出了後來成了中國文學研究大家的青木正兒的《以胡適為中心的湧動著的文學革命》的長文, 1922年出版的《文學革命和白話新詩》(大西齋等編著)收錄了胡適、康白情等人的作品,1920年抵達北京的基督教神父清水安三在1924年出版的《支那的新人和黎明運動》一書的第十章即為《現代支那的文學》,他雖然不是一個文學研究家,卻以自己在北京的實際感受向日本讀者傳遞了最新的信息。此後,村松梢風的《魔都》、谷崎潤一郎的《上海交友錄》等都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國文壇的新動向,1926年7月,當時在日本影響頗大的《改造》雜誌出版了夏季增刊“現代支那號”特輯,收錄翻譯了五四以來出現的新小說、新戲劇、新詩和評論等,應該說,時至1920年代末期,日本的文學界已經註意到了中國文壇的新氣象。但是在中國文學研究界,尤其是作為最重要的學術重鎮的帝國大學內,對中國的研究基本上依然沈湎於故紙堆裏。
於是,竹內好決定聯合身邊的同誌來創辦一個無論從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上來說都是一個嶄新的學術團體。這一想法大約產生於1933年後半期,經過數次的醞釀後,1934年3月1日在竹內好家裏,舉行了中國文學研究會第一次的準備總會。決定研究會的名稱為中國文學研究會,每月1日、15日舉行兩次例會,並出版一份研究雜誌《中國文學研究月報》。
當時研究會成員通過設在東京神田北神保町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內的書店,田中慶太郎開設在東京本鄉的文求堂書店,以及在北京的日本友人購入了大量中國新書刊,通過這三個途徑,研究會的成員幾乎讀到了所有當時中國出版的重要文學書刊,包括沈從文、老舍、茅盾、洪深、田漢、丁玲等的最新作品。
期間和之後,竹內陸續結識了後來成為研究會重要成員的小田嶽夫(小說家,《魯迅傳》和《郁達夫傳》的作者)、松枝茂夫(中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周作人作品和《紅樓夢》的譯者)、增田涉(中國文學研究家,翻譯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譯者)。
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主心骨無疑是竹內好,發起人是他,具體的經營乃至雜誌的編輯也是他,1937年,竹內好經日華學會的友人的斡旋,獲得了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資助,得以到北京去留學兩年,幾乎在同時,武田被應徵入伍,作為輜重兵的一員被派往中國大陸戰場。在竹內逗留北京的兩年期間,雜誌的編輯主要由松枝茂夫來擔任,1939年10月,竹內期滿歸國,重新接掌了研究會的日常工作。1940年4月,《中國文學月報》在出版了第59號之後,決定自第60號起改由生活社出版發行,刊名改為《中國文學》,頁數由原本薄薄的12頁改為48頁,對外公開發售。
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活動和成果主要表現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舉行研究例會、懇話會、講讀會等活動,就某一主題討論介紹研究會內外人員的相關研究心得和學術信息等。第二就是出版研究刊物,對當時魯迅、林語堂、沈從文、郁達夫等作家做了及時的介紹和評論,除了文學研究之外,對當時中國現實的社會也相當關註,蔡元培去世時,特別出版了紀念專輯。第三,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介紹。幾乎所有研究會的主要成員都是翻譯家,他們除了在《中國文學》上發表譯作外,幾乎都有各種翻譯的單行本問世,比較重要的有岡崎譯的丁玲的《母親》、郁達夫的《沈淪》、巴金的《寒夜》、沈從文的《邊城》等,而竹內好是日本最知名的魯迅翻譯家,以一人之力編選翻譯《魯迅文集》,可惜在完成了第6卷之後不幸去世。

在日本國內形勢越來越嚴峻的1943年,竹內好為了不使中國文學研究會失去自己的獨立品格,不得不忍痛解散了這一組織。在戰後,曾經一度恢復,也繼續出版刊物,但在1948年還是偃旗息鼓了。
不過,中國文學研究會在近現代日本對中國新文學的翻譯、介紹和研究上,影響是巨大的,在當時和戰後,主要的成員都成了著名的思想家(竹內好)、文學家(武田泰淳)和翻譯家(松枝茂夫)等,可謂功勛卓著。1977年,汲古書院復刻了所有的《中國文學研究月報》和後來的《中國文學》,他們在中日文學交流上做出的卓越貢獻,至今仍然令人敬仰。
① 竹內好《孫文觀的問題點》,初刊於1957年6月號《思想》雜誌,《竹內好全集》第5卷,第25頁,東京築摩書房1981年。
② 竹內好《作為方法的亞洲•序章 我的回想》,第16頁,東京創書社,1978年。
③ 武田泰淳《司馬遷•自序》,東京日本評論社1943年,此處引自《武田泰淳全集》第10卷,第3頁,東京築摩書房197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