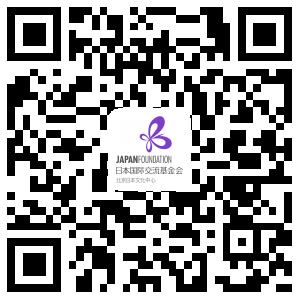《性欲与诗歌的创造力:日本诗人伊藤比吕美在德语世界的反响》

2024年是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年份,作为纪念活动之一,我们将邀请诗人、小说家伊藤比吕美女士于3月10日~17日来华访问,进行巡回演讲。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伊藤比吕美女士的作品,我们分两期,发表两篇关于伊藤比吕美女士诗歌、散文、小说的评论。
今天发表第二篇:《性欲与诗歌的创造力:日本诗人伊藤比吕美在德语世界的反响》,作者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伊尔梅拉·日地谷(Irmela Hijiya-Kirschnereit)教授。日语原文发表于《现代诗手贴》2005年6月号。
性欲与诗歌的创造力:
日本诗人伊藤比吕美在德语世界的反响
(「性欲と詩的創造力―ドイツ語圏における伊藤比呂美」)
伊尔梅拉·日地谷
(Irmela Hijiya-Kirschnereit)
没有什么比诗歌翻译更难的了。将学术或技术文章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最重要的是将内容以简明易懂的形式准确地转换为目标语言。文学的翻译不仅要求内容完整准确,还需要有形式的呼应,两者几乎是一体的,不能分割。诗歌是文学中一种高度凝练的表达方式。诗歌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目标语言的受众是否将译作视为诗歌,而不仅仅是内容的转述。
诗歌翻译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诗歌体裁的形式限制。内容越简洁,诗歌本身越优秀,越是包含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元素,至少其中有些内容与特定的文化基因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也很难让目标语言的受众立即理解。如果在文本中加入大量注释和文字说明,使这些诗歌更容易理解,就可能破坏诗歌作为一首诗的效果。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理想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在目标语言中能达到诗歌效果的作品,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兼顾目标语言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对原作艺术魅力的干扰。
要想知道作品的文化差异是否是目标语言受众接受它的主要因素,或者译作是否能够产生普遍的诗歌效果,一个办法就是仔细研究对它的评论。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评论家们阅读作品,这自然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对于一个此前籍籍无名的外国诗人。此外,许多评论家可能会对自己不太熟悉的外国文学底气不足,发表评论时会比较谨慎,笔锋也倾向于内敛和保留,尽量避免棱角分明的评论。无论如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欧国家的日本文学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翻译日本文学的作品数量增加,作品的类型和风格也更加丰富,书评的论调相较以前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1993年,我从伊藤比吕美几本著作中精选出诗歌和散文,将其译成德文,作为奥地利Residenz出版社著名丛书之一出版。该书的受欢迎程度远超我的预期,仅我所知道的就有14篇书评登载在报刊杂志上,广播节目也进行了介绍,这些显示了反响之强烈。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伊藤比吕美的诗歌在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等德语国家到底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大部分书评的标题和副标题都如实地反映出伊藤比吕美的诗歌给中欧人带来的强烈冲击,也展现出了评论家们对其作品的态度。德国《每日镜报》的标题是《震撼读者的日本诗人伊藤比吕美》;《南德意志报》的评论家则称她“摘下樱花这层面纱”;奥地利《标准报》的标题是《直视令人恐惧的事物》;德国《新时代》杂志的标题是《用文字进行杀戮:伊藤比吕美以激进的开放性震撼读者》;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报》的标题则是《死亡:来自日本的大师(Meister,引用保罗·策兰的著名诗句)伊藤比吕美的残暴与压抑之诗》。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伊藤比吕美的诗歌主题和表达方式激进,会激起人们的内心共鸣甚至是反感,但评论家们却无一例外地对伊藤的文学立意及其表达方式给予了肯定。而且几乎是所有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评论家们在自己的书评中提醒读者注意伊藤诗歌中隐含的阐释上的陷阱。《新时代》杂志的评论家说:“被彻底摧毁的不仅仅是血淋淋的现实。伊藤以细腻的口吻写下的粗俗语言也打破了德语读者对日本文学的刻板印象。伊藤的诗歌不是娇艳的樱花,而是语言的杀戮。”奥地利《标准报》的评论家对诗人伊藤比吕美的创作力表示钦佩,并做出了如下结论:“与她的激进主义相比,目前欧洲流行的女性主义批评虽具有合理性,但难以望其项背。”《南德意志报》的评论家表示,伊藤提供的不是“无情的幻灭文学、暴露心理学或假惺惺的教育学。”伊藤的作品“缺乏”与“可以称为日本文学传统的极简美学”的关联性。《新苏黎世报》的评论员写道:“我带着抵触,甚至是反感拿起这位40岁诗人的书。”“伊藤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条件下,对所有的事物进行了切割。伊藤的切割非常完美,就像用高科技做了一场手术一样,几乎没有流血。她的记录似乎完全没有任何情感背景,但却充满了出人意料的隐喻,这使得她的文章具有多义性。在反复阅读之后,读者发现对她的诗歌的理解会截然不同。女性的性欲与诗歌的创造力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的形式。”评论家们完全注意到了伊藤诗歌震撼人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出了与《新苏黎世报》的这篇书评相同的结论。而日本文学在此时也完全摆脱了一直以来的那种具有异国情调的、娇嫩的、需要戴着天鹅绒手套小心触摸的形象,理所当然地仅仅被视为“文学”了,因为伊藤比吕美的诗歌并不是从遥远的世界断断续续传来的“异国信号”。
1999年,同样由Residenz公司出版了伊藤比吕美的第二本书,但译者不同。书名是《家庭的医学》,由伊藤与西成彦合著,其中对童话和讲经歌谣等进行了重新诠释。该书的内容似乎也给评论家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与伊藤第一次相遇的经历似乎很好地帮助他们应对了这一冲击。其反响也出乎意料地好。评论家认为,两位作者的目的都是质疑并希望打破家庭是舒适安全的这一传统观念。但是,《波恩新闻总汇报》的评论家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他认为这本书“聪明的、有时甚至刁钻的反浪漫主义”是有局限性的,批评了两位作者作品中完全随意、甚至强行穿梭于德国、日本两国的童话和文学作品的方式。他在评论中屡次指出他们的作品与卡夫卡的《变形记》有关,也表示并不看好他们对于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和各种体裁略显粗暴的直接引用和间接挪用。《温特图尔信使报》的书评侧重于日本社会的演进和家庭问题。评论家指出,夏目漱石早在1905年就预言了家庭的崩溃,这本书可以视作这一社会变动的记录。但与此同时,伊藤和西成彦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庭内部的问题始终大同小异。他们在作品中对家庭和童话这一主题的处理方式饱含幽默和诙谐,作者们“不惧任何禁忌的、非日式的直接”态度似乎使评论家忘记了这本书的缺点。
虽然前面提到的一则书评中批评了本书“随意”在各种体裁之间穿梭的做法,但《柏林报》的长篇书评反而称赞了这一点。因为这本书“极具优雅,充满才气”,是非常“机敏”的作品,它驱使伊藤和西成彦的读者们“愉快、高兴地成为他们的观点和分析的帮凶”。通常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总是以方便讲述者的方式推进的,而童话则是由照顾孩子的母亲讲述的。根据伊藤和西成彦的说法,在童话中造成问题的总是女性。正是这些女性,疲惫而痛苦的母亲,给孩子们讲述故事,让他们陷入恐惧之中。作者似乎和读者一样享受着这种混乱的思考过程。这位评论家说道:除此以外,作者二人的分析还包括了对自我的幽默讽刺,这些自嘲使得本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学上都是一部极具独创性的作品。
以上这些是伊藤比吕美两本著作在德语国家的部分反响,清楚地表明她的文学作品受到了欢迎。与吉本芭娜娜、村上春树相比,伊藤比吕美作品的读者群不同,作品销量自然不能与这两位作家相提并论,这一情况在日本也是相同的。但是,作为诗人,她似乎已在德语世界站稳了脚跟,即使是那些认为她的作品过于激进的人,也会认真看待她的作品。我衷心希望她的文学作品在世界上其他语言圈也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也许在不同的语言圈,人们对伊藤的诗歌和散文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的文学体验以及他们对阅读的期待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会有很大差异。我非常好奇他们将如何看待伊藤比吕美的文学作品。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