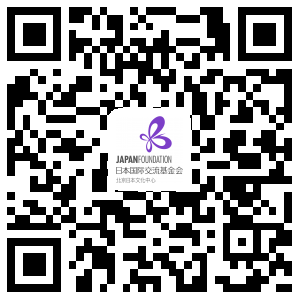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2) 第五讲:文学史重构视域…

*扫描或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文的繁体字版文本。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五讲:文学史重构视域下的黄瀛诗歌

主讲人介绍:
杨伟,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所长,日语系教授,文学博士。现任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日本私小说研究会特别研究员,曾在东京大学、法政大学、奈良教育大学等任客座研究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铜锣>同人草野心平、黄瀛、宫泽贤治研究》。出版有《日本文化论》、《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人》等个人学术专著,译有《人间失格》、《空翻》、《夕子的近道》、《他人的脸》、《镜子之家》等20余部文学名著或学术著作,主编《诗人黄瀛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上、下)》、《文化·越境·表象——中日文化交流研究》、《语言·民族·国家·历史》等学术著作,并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读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黄瀛先生1924年青岛日本中学毕业照
黄瀛从少年时代起便醉心于日语诗歌创作。1925年9月,年仅19岁的他在几千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荣登《日本诗人》“新诗人号”的首席,以明朗阔达的诗风一举成为诗坛的宠儿,后于1930年和1934年出版了日语诗集《景星》和《瑞枝》,是第一个在日本近代诗坛上赢得卓越声誉的中国诗人。他还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诗人一起创办了诗歌杂志《铜锣》,且与诗人高村光太郎、小说家井伏鳟二等都有过文学上的亲密交往,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但颇为奇怪的是,黄瀛在战后遭到了日本文坛的遗忘,直到苍土舍1982年推出《瑞枝》的复刻版,1984年出版《诗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才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小小的黄瀛热。1994年佐藤龙一作为生前采访过黄瀛的传记作家,掌握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传记《黄瀛——他的诗及其传奇生涯》(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1994年),为黄瀛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史实资料与大致的年谱。而在安藤元雄等主编的《现代诗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中,也专门收录了“黄瀛”词条。这些都表明,黄瀛作为卓有成就的日语诗人,也作为一个有着跨文化身份的传奇人物,已引发了文学研究者和史学家们的兴趣。但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成果还大都停留在人物传记或文坛忆旧的框架内,并没有完全改变黄瀛诗歌在日本现代诗歌史上的边缘地位和遭到日本诗坛日渐遗忘的事实。
当然,要一一追溯黄瀛被日本诗坛遗忘的原因或许并不那么简单,但正如冈村民夫指出的那样,“这一重大的缺失既不是因为其诗歌水平的低下,也不是源于其原创性的匮乏,更不是因为其缺乏现代性,而毋宁说是因为其诗歌创作的核心潜藏着语言、文化以及存在论上的‘越境与混血’”[1]。换言之,这种由“越境”和“混血”所表征的诗歌特质作为一把双刃剑,在造就了其他诗人所无法模仿的特殊魅力的同时,也使他的诗歌成为了一种有些异端的少数文学,从而很容易被关闭在主流诗歌史的门外。
而追溯另一个原因,或许与黄瀛在诗坛上的微妙地位不无关系。比如,作为混血儿,他无疑是诗坛的“单独者”,但却又不甘寂寞,广泛参与了各种主张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诗歌团体。尽管不是团体的中心人物,但反倒赢得了不受束缚的自由,可以逾越团体的界限,而成为诗坛的自由人士。比如,他既是《铜锣》杂志的同人,也是《碧桃》和《草》等杂志的成员,同时还大肆活跃在《诗与诗论》等追求纯粹诗的现代主义诗刊上。他这种在诗歌团体上的越境性不仅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某个特定诗派的柔韧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导致很难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位和评价。此外最重要的一点,“还得归咎于我们一直以来习惯于把日本文学视为‘日本人的文学’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2],因此,身为中国国籍的黄瀛被摒弃在“日本文学”之外,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日语文学”这一概念。这显然与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包括亚洲人和欧美人在内的外国人用非母语的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潮大有关系。对这些外国人用日语创作的文学进行研究,已俨然形成了一股引人瞩目的潮流。如果从“日语文学”的视域重新审视黄瀛及其诗歌,我们不能不说,像彗星般划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诗坛的黄瀛不仅没有过时,毋宁说蕴含着历久弥新的价值,以至于黄瀛“在今天乃是应该被更广泛地知晓和重新评价的‘崭新’诗人”[3]。而“对诗人黄瀛的再评价,也能对‘日语文学’的拓展成为一种具有批评性和生产性的催化剂”[4]。
笔者注意到,在积极倡导对黄瀛及其诗歌进行评价的学者中,黄瀛的传记作家佐藤龙一认为,“不妨把黄瀛作为用日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给予更多的评价”[5]。而奥野信太郎则在《黄瀛诗集跋》中一边竭力主张在日本对黄瀛诗歌进行鉴赏和评价的必要性,一边不忘呼吁道:“作为一个深谙日语之神秘的中国诗人,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6]不难看出,与佐藤龙一把黄瀛看作是“日本诗人”不同,奥野信太郎是把黄瀛作为“中国诗人”来定位的,从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而这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之所以能够同时成立,除了恰好印证出作为混血儿的黄瀛身份的边界性和双重性之外,也很可能体现了两者在把握黄瀛特质时的不同诉求。笔者认为,当佐藤龙一主张把黄瀛作为“日本诗人”来定位时,他是希望把黄瀛诗歌作为日本诗歌的一部分来置于日本文学内部加以评价的,而当奥野信太郎把黄瀛定位为“中国诗人”时,则暗示了把黄瀛及其诗歌置于中国文学范畴内来进行考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显然,佐藤龙一和奥野信太郎在给黄瀛及其诗歌定位时为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视域,但笔者注意到,佐藤龙一所使用的“不妨把黄瀛作为用日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给予更多的评价”,其实是一个有所保留的句式,即是说,他是在充分意识到黄瀛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日本诗人”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种诉求,这一点可以从“不妨”这一带有倡议性质的表述中得到佐证。因为从国籍的归属上看,黄瀛乃是中国人,而并不是日本人,所以严格说来,“日本诗人”并不是对黄瀛的最准确定义。同样,奥野信太郎的表述也是值得玩味的,当他把黄瀛定位为“中国诗人”时,不忘用“深谙日语之神秘”这一修饰语强调了黄瀛作为“中国诗人”的特殊性,即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诗人”不同,黄瀛不是用中文,而是“借助了日语,才得以保持了与诗歌世界的联系”[7]。或许奥野信太郎深知,作为并非标准意义上的“中国诗人”,黄瀛被拒斥于中国诗坛之外亦属无可奈何,但也惟其如此,他的诉求才显得越发急迫:“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
笔者注意到,同时代的诗友们大都是以“口吃”、“混血”、“中介”、“越境”等为关键词来勾勒出诗人黄瀛形象的主要特质的。显然,“口吃”、“混血”、“中介”、“越境”等所蕴含的阈限性和模糊性在暗示了对黄瀛进行准确定位之困难性的同时,也预示了对黄瀛进行多种定位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可以循着佐藤龙一提示的路径,从日本文学的流变中来审视黄瀛及其诗歌的革命性力量。而无论是从“少数文学”,还是从“日语文学”的视域出发来评价黄瀛诗歌,都会带来对黄瀛诗歌的价值重估。而笔者注意到,在冈村民夫、佐藤龙一等黄瀛研究者们——尽管还为数太少——已经着手于把黄瀛诗歌置于日本文学内部来展开研究的今天,循着奥野信太郎的思路,把黄瀛作为中国诗人,将其诗歌置于同时代中国新文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评价,或许同样具有可行性和生产性。
就像黄瀛因中国国籍而被排斥在正统的日本文学史之外一样,黄瀛的诗歌由于是用日语创作而成,从而阻碍了其在中国诗坛的流通。再加上黄瀛1930年底回国后一直从戎,除了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有过数次短暂的见面之外,与中国文学界鲜有交集,解放后在文革中又惨遭迫害,致使其作为诗人的身份鲜为人知,因此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之外也并不奇怪。但我们知道,今天固有的文学概念正遭到解构,文学史的重构业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就像“日本文学”正由以前那种“日本=日本人=日语=日本文学”[8]这样一种粗暴的等式中逃逸,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概念一样,或许“中国文学”的定义也面临着解体与重构,而有可能摆脱“中国=中国人=中文=中国文学”这一封闭的定义,成为涵盖很多边缘性内容的概念。比如,像黄瀛这种身为中国人却用非中文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也不妨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像黄瀛诗歌这种处在“边界地带”的东西既是日本文学中的“少数文学”,同时也不妨视为中国文学中有些特殊的部分,或称为中国文学中的“少数文学”。诚然,黄瀛的诗歌是日语写成的,且充满了日本元素,甚至是远离中国文学传统的,但也正因为其中的异质性和边缘性,则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史的新视野。而与此同时,置于中国新文学发生、流变的历史语境中来把握黄瀛及其诗歌,也很可能让我们去重新发现黄瀛的价值和局限性。
比如,一旦把黄瀛诗歌与同时代的中国新诗,特别是创造社等留日派诗人的新诗相比,就会发现,尽管它们背后同样弥漫着因中日关系和国内形势的动荡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还有“支那人”等蔑称在心中唤起的作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从而使它们能够被置于同一时代坐标中加以相互比照,但与创造社诗人们“倾向于在整体的群类生存而非个人生存角度来感受问题,或者说个人生存的遭遇也被他们抽象成了民族整体的境遇”[9]不同,黄瀛似乎更倾向于从作为混血儿的个体性悲哀出发来感受问题,并把“支那人”的民族整体境遇具象化为“我”的个人遭遇来进行描写和抒发,既达成了对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中国在全球性境遇中屈辱地位的痛切体认,也获得了作为现代性个体的生命自觉和自我意识。换言之,他依靠将外在现实带来的不安转化为对个人身份的困惑和认证,不是通过向外高声呐喊,而是借助向内浅唱低吟来达成了内在心象的忠实描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黄瀛乃是中国新文学留日作家中少有地坚持从“个人本位”立场出发,自始至终关注着身份认同等现代性问题的艺术派诗人之一,从而丰富着中国新文学中留日派文学的宝库,让我们管窥到留日派文学中并不太多见但却确实存在的另一种姿态和可能性。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把大正时期至昭和初年称之为中日两国文学之间的“蜜月时代”,即两国文学者“彼此可以畅谈文学的幸福时代”[10]。从某种意义上说,黄瀛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铜锣》同人的文学交往就得益于这样一种“幸福的时代”,同时也成为佐证这一“幸福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在国家和战争的坚壁前却像鸡蛋般脆弱易碎的生动案例。

作为那个“幸福的时代”以及其后那场不幸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黄瀛的诗歌记录了他与日本诗人友好交往的温馨片段,也同时记录了在日本步入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其作为中日混血儿的不安、困窘和焦虑,以及最终达成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作为中国国籍的诗人,他用不同于普通日本人的日语所写成的诗歌勾勒出了其在中日两种语言、文化以及身份中游弋的轨迹,揭示出了遭到主流诗歌有意遮蔽或无意漏视的某些侧面甚或重要的细节,从而得以在与同时代的中心话语与主流叙事的对照中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并在日本现代诗歌史与中国新文学史的重构中化作具有生产性的鲜活一页。
黄瀛先生诗二首:
朝の展望[11]
見給へ
砲臺の上の空がかつきり晴れて
この日曜の朝のいのりの鐘に
幾人も幾人も
ミツシヨンスクールの生徒が列をなして坂を上る
冬のはじめとは云ひ乍ら
胡藤の疎林に朝鮮烏が飛びまはり
町の保安隊が一人二人
ねぎと徳利と包とをぶらさげて
丸い姿で胡藤の梢にかくれたり見えたり
あゝ朝は實に氣もちがいゝ
窓をふいてると
暖い風が入りこみ部屋をぐるぐるまはる
そしてあゝ
日曜の朝はいつにない陽の流れ
いつにない部屋の靜かさ
この二階の室で海から山から
僕は伊太利のやうなこの町の姿をも見ようとするのだ
寄宿舎で一番見晴しのよいこの部屋からは
はげ山の督辦公館も見え
その上にまた
信號所のがつしりした建物が見えて
このあさみどりの空に
數葉の旗がはたはたとなびき
ゆふべ一晩沖に吠えてゐた帆前船が
しづしづと
しづしづと港へ入るではないか
あゝ黒い保安隊の兵舎からは
すてきにゆるやかなラツパの音
海面一帯朝の光りに輝いて
軍艦海坼の黒煙りよ
それからまた遠い向ふ岸の白壁の民家よ
窓をふきながら
春のやうな氣分もて
こゝろしづかにも
日曜の朝の展望をするのだ
(译文)清晨的展望
瞧
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
随着这礼拜日清晨的祷告钟声
一群群,一群群
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排着队伍沿坡攀登
虽说是冬日的伊始
可喜鹊却在稀疏的洋槐林中四处飞旋
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
故意提拎着青葱、酒壶和包袱
蜷缩着身体,在洋槐林的树梢间忽隐忽现
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
一旦擦拭窗户
暖暖的风便鱼贯而入,在房间里来回盘桓
而且,啊——
礼拜日的清晨流泻着不同于平日的光线
还有房间里不同于平日的静闲
在这二楼上的房间远眺大海,远眺山峦
我还要尽览这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头景观
从这宿舍里风景最佳的房间
能望见秃山上的督办公馆
还有耸立在它上面的
信号所的坚实建筑
在这浅绿色的天空上
几杆旗帜呼啦啦地随风招展
在海面上吠叫了一夜的帆船
不是正静静地
静静地驶入了港湾?
啊,从黑黢黢的保安队宿舍
传来了美妙而悠闲的号角
海面在清晨的光影中烁烁闪闪
啊,海圻号军舰冒着黑烟
遥远的对岸耸立着白墙的民房
一边擦拭着窗棂
一边怀着春天的萌动
平心静气地
展望礼拜日的清晨
天津路的夜景
――青島回想詩――
ゆがんだ看板や
涼しいビスヰ屋なぞずらりと並べ
あの古びた獨逸町の
夕やみをくゞつて僕がしたしんだ天津路
あゝ天津路、天津路
いやにくらい銭舗の銅子兒の音や
ふとつた豚女や
ぽくりぽくり高底靴をはいた魚屋や青物屋の若者や
どこかのつぺりした官吏の少爺や
大きな布團を脊にした田舎出の苦力や
あゝ私は本當にあのころ天津路をむやみに歩いた
あのバタくさい青島の町で
しみじみと中國の生活にしたしむために
燕の飛ぶ夕やみをくゞつて
ゆがんだ金銀の看板をめでたり
清爽な晩香玉の香りを鼻にしたり
胡藤の花咲く山の中の
きうくつな中學寄宿舎をぬけ出して
さゝやかな料亭の一君子となつて
初夏の夕ぐれを愛した
一ぱいの蘭茶に
あの東洋的な天津路の夕景を
ぐつと心の中にのみいれて
自分は中國人だといふことを無上の光栄に思ふた
(译文)天津路的夜景
――青岛回想诗――
在那古旧的德国租界
挤满了歪斜的招牌
和清凉的翡翠商铺
我穿过它昏暗的暮色,赶往熟悉的天津路
啊,天津路,天津路
钱庄那阴郁得可怕的铜钱声
肥胖的女人
穿着筒靴的鱼铺子和蔬菜店的年轻伙计
不知是哪儿的面无表情的官少爷
还有背着大被褥、从乡下来打工的苦力们
啊,那时的我真是马不停蹄地走在天津路上
在青岛那散发着奶酪臭的街道上
为了熟悉中国的生活
我在燕子盘桓的暮色中穿梭
观赏着歪斜的金银招牌
闻着晚香玉清爽的芳香
我从山中开放着洋槐花的
令人窒息的中学宿舍里悄悄溜出
摇身变成小小饭庄里的一介君子
深爱着这初夏的黄昏
我品味着一杯兰茶
把充满东洋风情的天津路夕景
一口气啜饮进心中
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大江健三郎文学——在鲁迅的文学之光引导下前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金龙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2)
题目及主讲人
阅读繁体版↓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