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22年7月日本语能力测试(JLPT)报名的通知
2022年7月日本语能力测试将于7月3日举行,网上报名将于2022年3月14日开始。请考生认真仔细阅读报名网站的《考生须知》和《报名步骤》。
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建议考生报考本地考点的考试,并请仔细阅读和密切关注《日本语能力测试(JLPT)疫情防控须知》、《各考点疫情防控期间日本语能力测试(JLPT)入校要求》(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遵守所报考点的入校要求。如考点所在地区出现疫情,不排除考点根据当地政府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取消考试的可能。
中国大陆考生参加考试必须携带的唯一身份证件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任何中国公民无论是何年龄,均可向户籍所在派出所申领身份证。特别提醒未申领身份证的青少年考生提前办理,以免影响考试。请考生确认所持二代身份证仍在有效期内、芯片信息读取功能正常、本人当前相貌无重大改变(如整容、性别改变等)。否则,建议考生立即重新申请新的二代身份证。
| 地区 | 代号 | 考点名称 | 考点地址 | 电话 | 考点网址/公众号 |
| 具体考场地址,以准考证为准 | |||||
| 北京 | 1020101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010-88817840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100089 | |||||
| 1020103 | 北京语言大学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 | 010-82303550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100083 | |||||
| 1020105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 010-6577843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100024 | |||||
| 1020106 | 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三教,二教 | 010-62751581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100871 | |||||
| 上海 | 1020202 | 华东师范大学 | 上海闵行区 东川路500号 | 021-34756652,3475615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200062 | |||||
| 1020207 | 上海大学 |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新校区 | 021-66132028, 19101789013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00444 | |||||
| 1020209 | 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 | 上海桂林路100号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徐汇校区) | 021-64320641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00234 | |||||
| 1020210 | 东华大学外语学院 | 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东华大学(延安校区) | 021-62373740,67792243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00051 | |||||
| 吉林 | 1020301 | 吉林大学 | 吉林大学 | 0431-85151636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130023 | |||||
| 1023601 | 延边大学 |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977号延边大学 | 0433-2732561,243655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133002 | |||||
| 辽宁 | 1020401 | 大连外国语大学 | 大连外国语大学旅顺校区(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6号) | 0411-86115161, 0411-86115162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116044 | |||||
| 1020403 | 大连理工大学 | 大连市甘井子区凌工路2号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 0411-84707329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116024 | |||||
| 1020404 | 大连大学 |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学府大街10号大连大学 | 0411-87403639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116622 | |||||
| 1020601 | 辽宁大学 |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66号崇山校区蕙星楼、东配楼 | 024-62202260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110036 | |||||
| 1020602 |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253号 | 024-8659253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110034 | |||||
| 广东 | 1020501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校区 |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2号广外北校区 | 020-36207153/7580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510420 | |||||
| 1020503 | 中山大学 |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 020-84110970,84113240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510275 | |||||
| 1022302 |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 深圳市西丽镇留仙大道(西校区) | 0755-26019721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518055 | |||||
| 1020504 | 广州商学院 | 广州市黄埔区九龙大道206号康大教育园广州商学院 | 020-32975019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511363 | |||||
| 天津 | 1020701 | 天津外国语大学 | 天津外国语大学逸夫教学楼 | 022-23243358; 022-2328608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300204 | |||||
| 1020703 | 南开大学 | 天津市南开大学第二主教学楼 | 022-23503696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300071 | |||||
| 黑龙江 | 1020801 | 黑龙江大学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74号黑龙江大学 | 0451-86608579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150080 | |||||
| 陕西 | 1020901 |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 西安市咸宁西路28号 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 | 029-8266811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710049 | |||||
| 1020902 | 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 | 西安郭杜教育技术产业开发区文苑南路 | 029-8530938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710128 | |||||
| 1020903 | 西北工业大学 | 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西北工业大学诚字楼 | 029-8849452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710072 | |||||
| 重庆 | 1021001 | 重庆市四川外语大学 | 重庆沙坪坝区烈士墓壮志路33号四川外语大学 | 023-65385440,65385298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400031 | |||||
| 山东 | 1021101 |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 | 济南市文化东路山东师范大学 | 0531-86180084/8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250014 | |||||
| 1021101 |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湖校区 | 济南市长清区大学路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校区 | 0531-86180084/8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50315 | |||||
| 1021102 | 山东大学 |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公教楼 | 0531-88377517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50100 | |||||
| 福建 | 1021301 | 厦门大学 |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 | 0592-2181317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361005 | |||||
| 1024101 |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服务中心 |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考试服务中心(福州通湖路后槽13号) | 0591-87668908,8766890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350001 | |||||
| 浙江 | 1021401 |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 | 0571-88273293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310028 | |||||
| 1021402 | 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 | 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18号,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 | 0571-88066397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310012 | |||||
| 1021403 | 浙江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绍兴市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 绍兴市柯桥区越州大道958号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考场 | 0571-96399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310012 | |||||
| 1022701 | 宁波大学 | 宁波市风华路818号宁波大学教学楼 http://ffl.nbu.edu.cn/ | 0574-87600022, 0574-87601650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315211 | |||||
| 1024301 |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 绍兴市会稽路428号F幢教学楼 | 0575-8911435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312000 | |||||
| 内蒙古 | 1021501 | 内蒙古中日友好语言培训中心 | 内蒙古大学 | 0471-3462789 | 公众号:内蒙古中日友好语言培训中心 |
| 10080 | |||||
| 河南 | 1021601 |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广文路2号院(广文路与建设路交叉口) | 0379-69843766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471003 | |||||
| 1024501 | 信阳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产业集聚区发展大道1号教学楼、2号教学楼 | 0376-2793397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465500 | |||||
| 江苏 | 1021701 | 苏州大学 | 苏州大学校本部、苏州大学东校区(本部和东校区有桥相连) | 0512-6511210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215006 | |||||
| 1021702 | 苏州科技大学 | 江苏省苏州市新区滨河路1701号 | 0512-69379107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15011 | |||||
| 1022101 |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 南京四牌楼2号(四牌楼校区) | 025-8379225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10096 | |||||
| 1022102 |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宁海路122号) | 025-83732062,025-83598582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10097 | |||||
| 1022801 |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 无锡江南大学第一教学楼 | 0510-8591998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14122 | |||||
| 1023301 | 扬州大学 | 江苏省扬州市华扬西路196号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 | 0514-8797166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25127 | |||||
| 1022802 |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 无锡市新区新锡路8号教学区内 | 0510-85342501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14028 | |||||
| 1023901 | 南通大学 | 江苏省南通市啬园路9号南通大学主校区方肇周楼群 | 0513-85015963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26007 | |||||
| 1023902 |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 江苏省南通市江通路48号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教学楼 | 0513-51001509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226011 | |||||
| 四川 | 1022001 | 四川大学 |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133号 四川大学(望江校区) | 028-85464311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610065 | |||||
| 1022002 |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 |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航空港校区)第四教学楼 | 028-8581368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610225 | |||||
| 江西 | 1022401 | 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 南昌大学前湖校区 | 0791-83969477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330031 | |||||
| 河北 | 1022501 |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 石家庄河北师大新校区公共教学楼C座 | 0311-80788519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50024 | |||||
| 1023801 | 保定市剑桥英语学校 | 保定市莲池区七一东路未来像素1号楼803室(考点办公室地址) | 0312-3150005/5958753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 71000 | |||||
| 山西 | 1022601 | 山西大学 |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 0351-7011732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30006 | |||||
| 贵州 | 1022901 |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 贵州省贵阳市贵州大学花溪区北校区 | 0851-8829024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550025 | |||||
| 广西 | 1023101 | 广西大学 | 广西大学西校园第一教学楼 | 0771-3237226, 18076340242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530004 | |||||
| 云南 | 1023401 | 云南师范大学 |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雨花片区1号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 0871-65911774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650500 | |||||
| 海南 | 1023501 | 海南大学 | 海南大学十号教学楼 | 0898-66279168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570228 | |||||
| 甘肃 | 1023701 | 兰州大学 |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199号兰州大学医学校区杏林楼 | 0931-8912115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730000 | |||||
| 安徽 | 1022202 | 安徽三联学院 |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安路47号 | 0551-63830750 | 点击查看详细要求 |
| 230601 |
日本语能力测试 (JLPT)证件要求:
- 中国大陆考生参加考试必须携带的唯一身份证件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任何中国公民无论是何年龄,均可向户籍所在派出所申领身份证。特别提醒未申领身份证的青少年考生提前办理,以免影响考试。请考生确认所持二代身份证仍在有效期内、芯片信息读取功能正常、本人当前相貌无重大改变(如整容、性别改变等)。否则,建议考生立即重新申请新的二代身份证。
- 中国香港和澳门考生必须携带有效的港澳身份证原件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原件参加考试。
- 中国台湾考生必须携带有效的台湾地区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原件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原件参加考试。
- 非中国籍考生必须携带有效护照原件参加考试。护照明确显示考生的姓名、本人近期照片和签字,并带有中国入境签证(中国给予免签证待遇国家的护照除外)和中国边境入境签章。
如果您的身份不符合上述条件,请于注册用户前联系报名中心咨询。
JLPT网上报名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考生仅进行个人信息注册和上传电子照片;第二阶段除考生可继续注册外,按N1、N2、N3~N5的顺序依次分别开放考试名额供已完成个人信息注册与上传电子照片的考生选择级别和考点,此阶段要求考生完成预定考位和支付考费等全部报名手续。
网上报名开通时间的具体安排如下:
| 阶段 | 具体步骤 | 日期及时间 | |
| 开通日期 | 截止日期 | ||
| 报名 | 1、注册个人信息2、上传电子照片 | 2022年3月14日 14:00 | 2022年3月30日 14:00 (逾期不予补报) |
| N1 | 2022年3月21日 14:00 | ||
| N2 | 2022年3月22日 14:00 | ||
| N3~N5 | 2022年3月23日 14:00 | ||
| 考试前 | 打印准考证 | 2022年6月27日 14:00 | |
| 考试当天 | 考试日期 | 2022年7月3日 入场截止时间为下午13:10 | |
| 考试后 | 成绩单 | 考试结束后3个月左右到达考点,各考点成绩单和证书保存时限为两年,请考生合理安排领取时间 | |
本次考试开始增加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考点。
2022年3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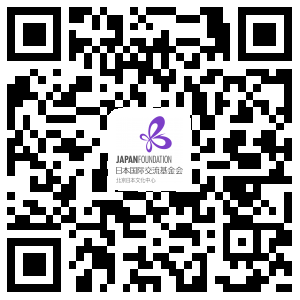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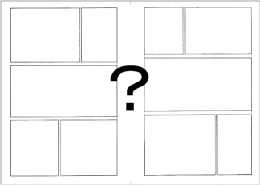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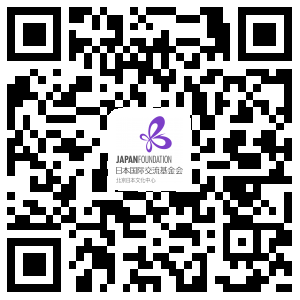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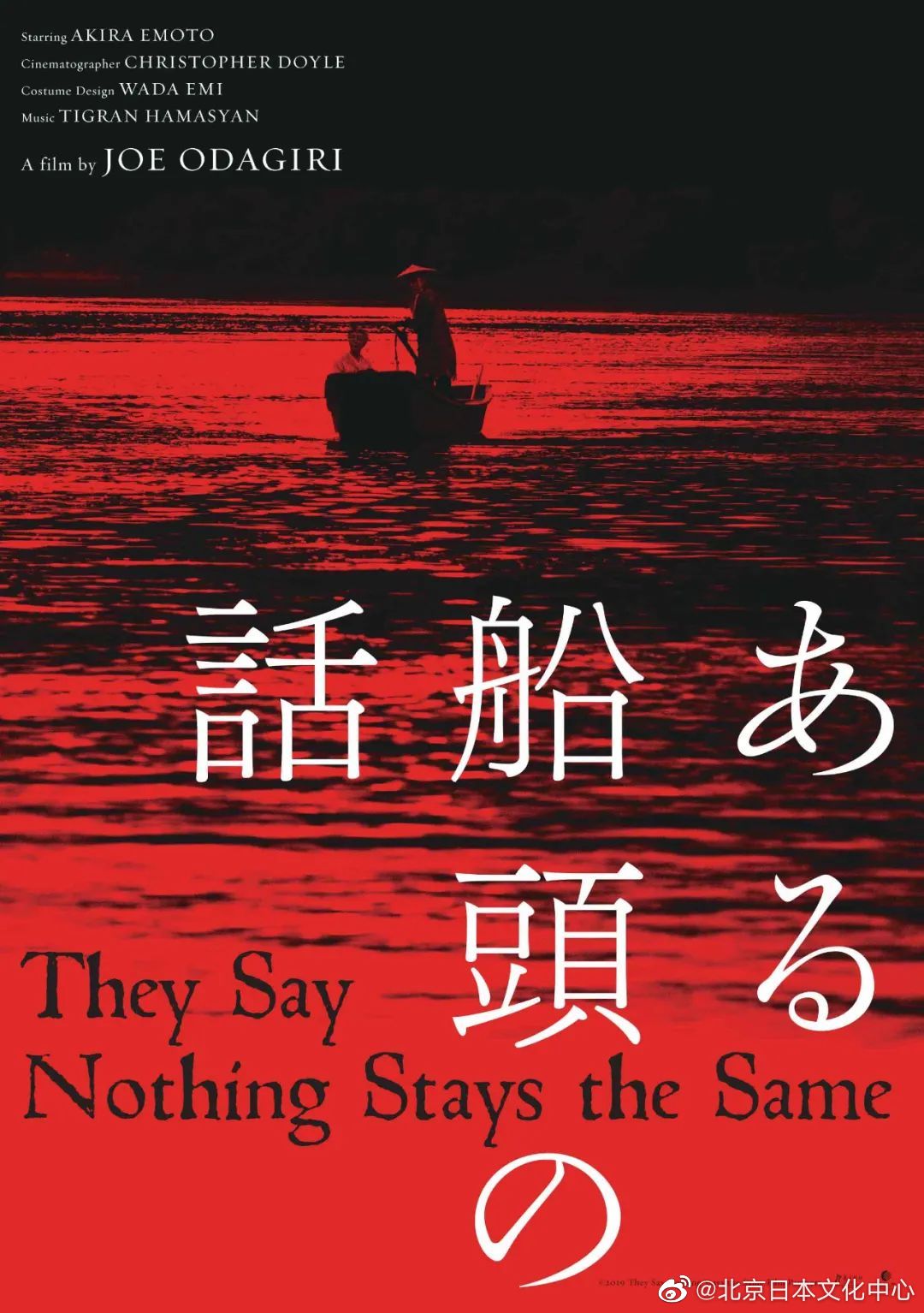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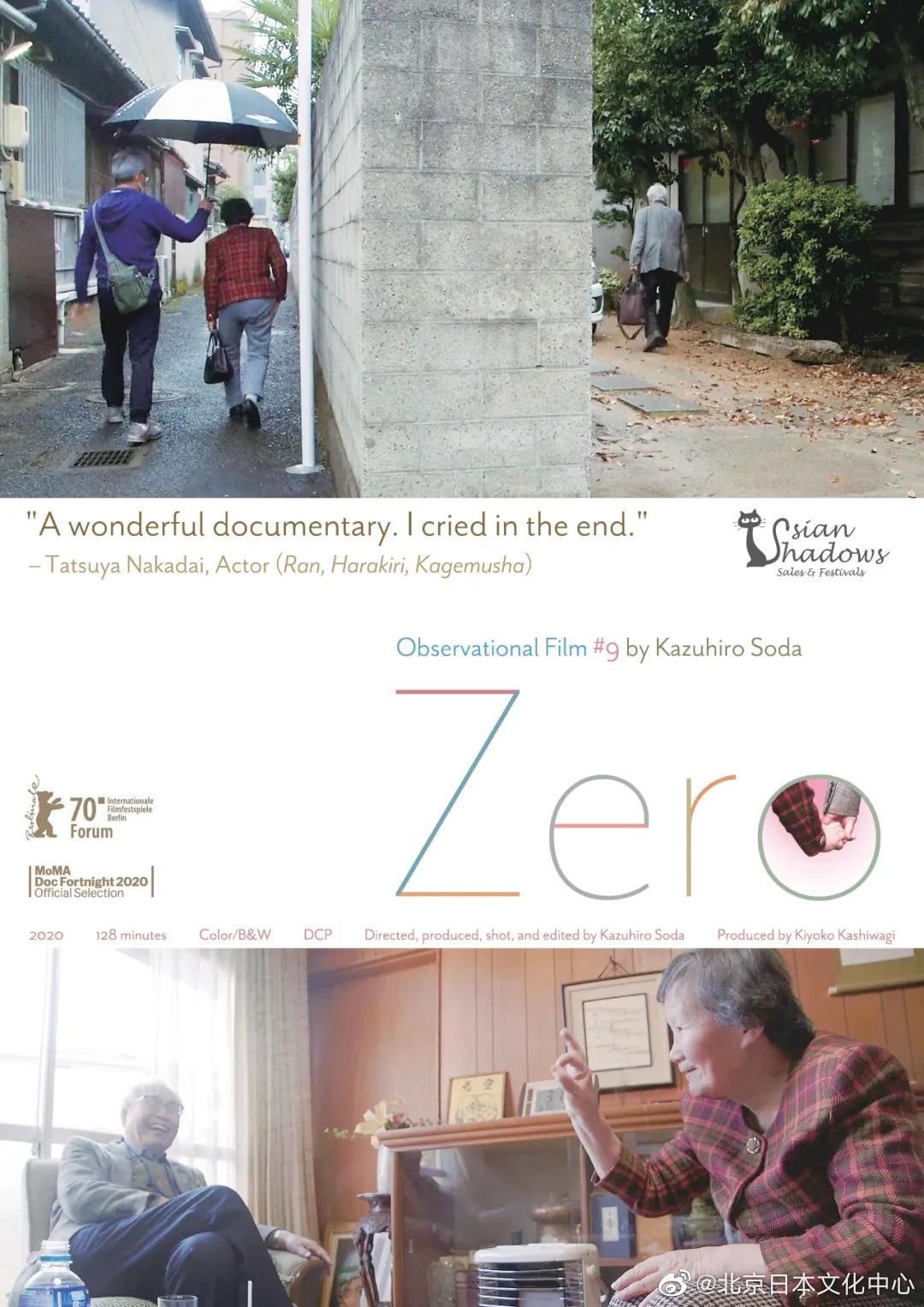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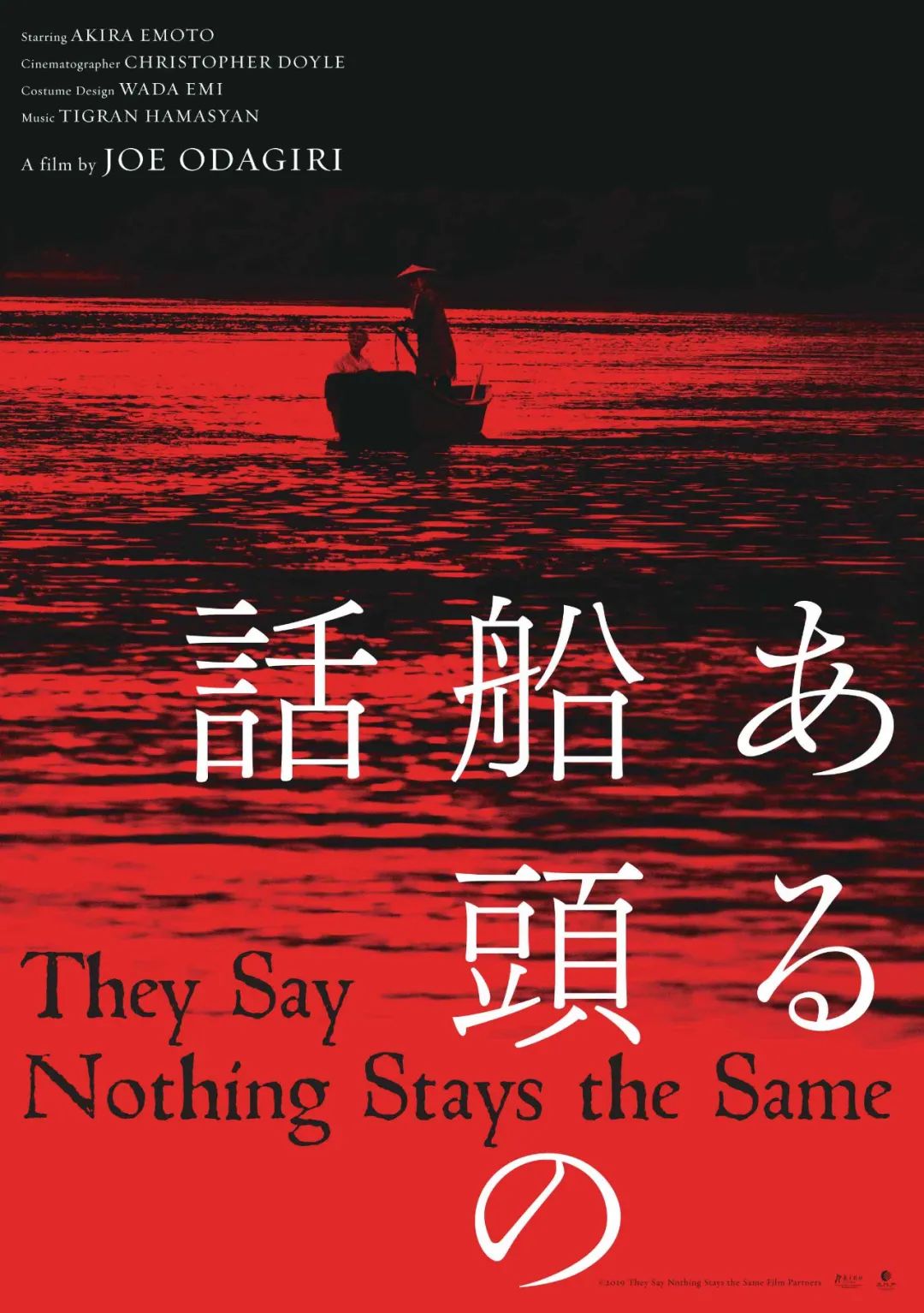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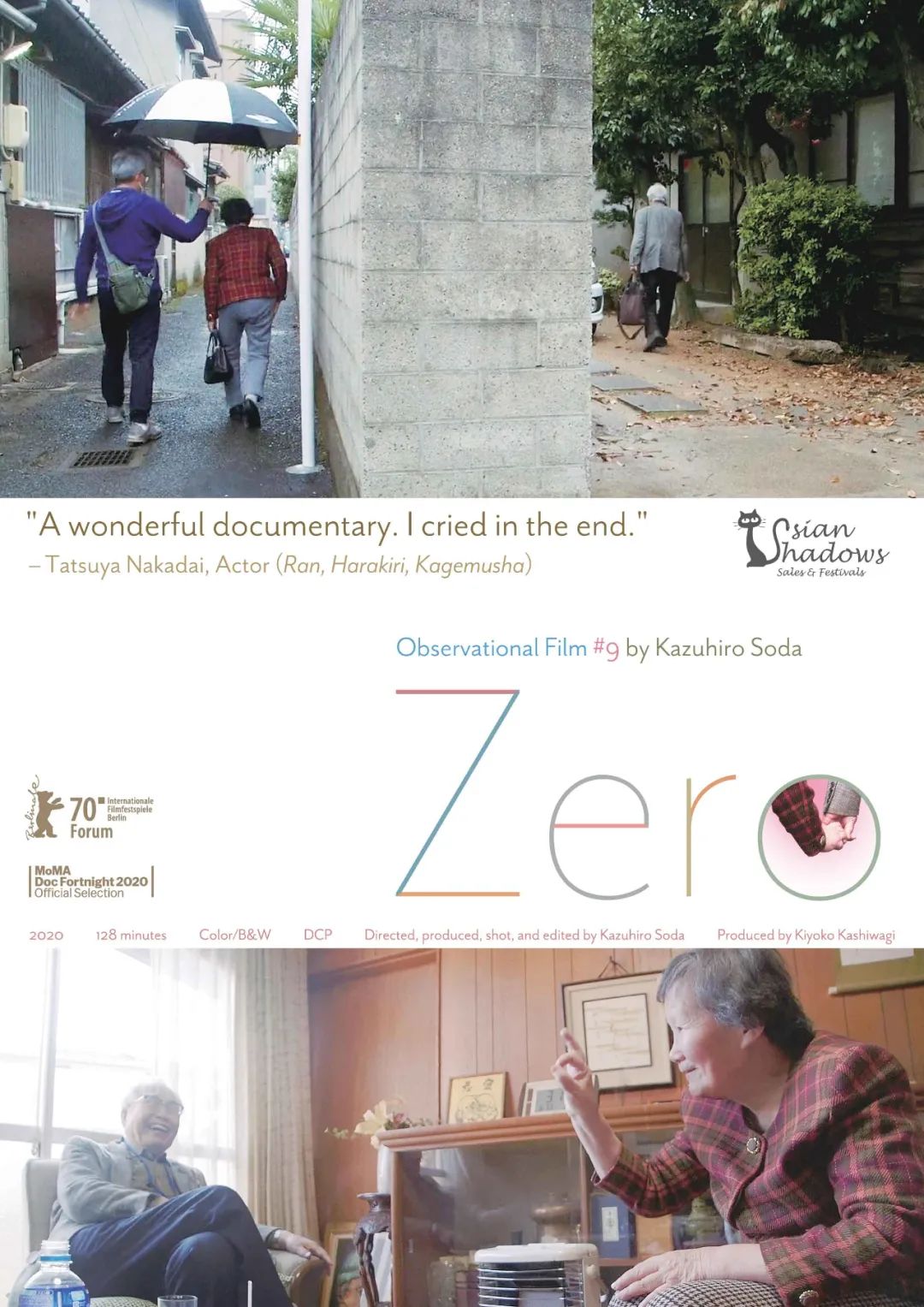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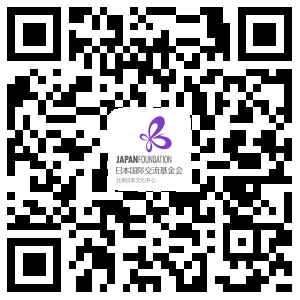
-5.jpg)

